分类导航 / Navigatio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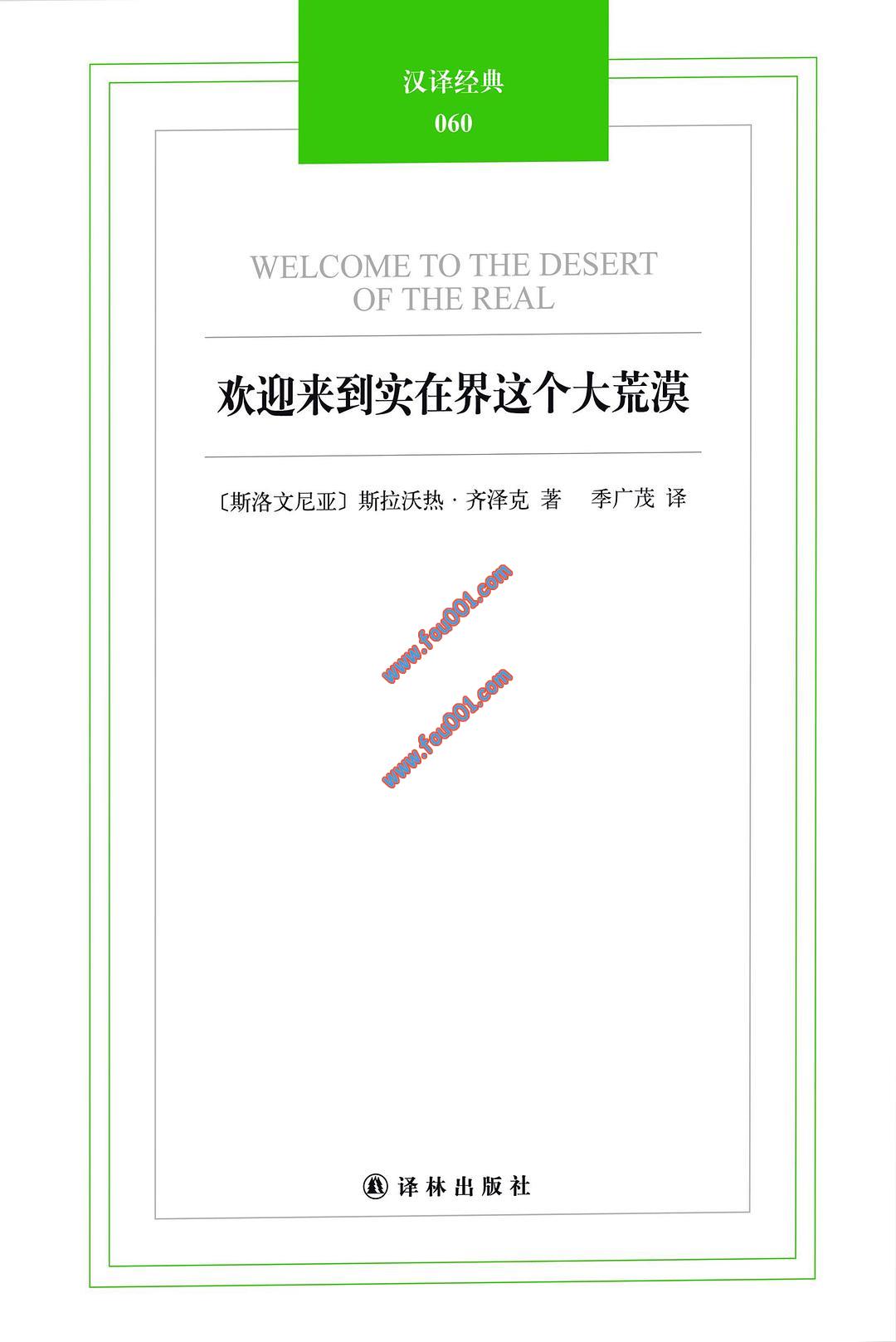 商品详情
注意:链接有问题的书请登录邮箱查收!!!
即时起网站不再提供充点下载服务,点数没有使用完的顾客需要什么书请直接联系客服!! 此书为PDF电子版,不是纸书,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质书籍,下载24小时内请删除!本站展示只是部分图书,如需别的电子书请联系客服! 购买时请填写真实邮箱。邮箱请填写正确并请填写常用邮箱! 电子书购买后不予退款。 切记,付款完成后不要关闭网页,等自动返回。如遇链接失效或密码错误,请于24小时内登录购买时留下的邮箱查收文件。 成功付款,但没有弹出下载地址请联系客服处理。不主动联系客服产生的损失请自负。 即日起网站开通VIP会员,VIP会员直接购买打八折,VIP会员购书流程: 1.注册本站会员 2.登录网站,进入会员中心,点击左边导航“在线充值”,选中“购买VIP会员”,再点充值并付款,完成VIP会员购买。 (链接地址为:http://www.fou001.com/e/member/buygroup/) 3.确认选购的电子书,点立即购买,填写收货人信息,填入优惠码:ODAE4VYFG5UJJDXQWDHH 4.下一步,付款,完成购买
书名: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副标题: 作者:季广茂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32185 出版时间:2012 页数:186 定价:20.00 内容简介: 2001 年美国发生“9 · 11 恐怖袭击事件”后,各色人等纷纷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做出回应,本书则透过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和生命政治的视角对这些回应进行回应,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实在界” 本指饱受战争蹂躏的荒漠地貌,在作者那里,它却成了 20 世纪人对实在界充满激情的完美例证; 表面看来, “9 · 11 恐怖袭击事件”乃原教旨主义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猛烈反扑,而在作者看来,两者是不折不扣的难兄难弟: 原教旨主义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淫荡的超我补充” 。本书视角新颖,见解独特,令人拍案叫绝。 斯拉沃热·齐泽克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资深教授,美欧众多大学及研究机构客座教授,欧陆哲学家和批判理论家。自称“还算合格的共产主义者”和“激进左翼分子” 。深受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影响,擅长以通俗文化产品解读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以拉康精神分析理论、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最新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现象。1989 年出版《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后,迅速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也被称为 “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和 “欧洲青年知识分子先锋的偶像” 。 这套丛书还有 《阿兹特克文明》,《艺术的意味》,《圭恰迪尼格言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理想国》 等。 要真正忘记某件事件,首先要竭尽全力,牢牢记住它。生存于一个被建构的世界中,记住和忘记由不得自己,终究还是一套官方的意识形态罢了。 还是那句话人若不能活在自己创造的概念中将会多么的可怜弱小又无助,千万不要自己跑到实在世界的大荒漠哦。书里看到了德勒兹和克尔凯郭尔。所以我认为必须要看看克尔凯郭尔了。 尽管是一本哲学书,但普通读者其实是不必担心本书太过艰涩而难以阅读的。事实上,齐泽克的这本作品的面向,恰恰是非专业的读者——本书所阐释的重心,是人们看待世界可以采取的方式,而非观测世界的结果。 当然,在阅读本书之前,读者还是需要储备一些知识的。这本书最关键... (本文已發表於《南方論叢》2009年3月第一期,頁100-111。) 論文摘要: 齊澤克(Slavoj Žižek)曾在一次訪談中,明確表明他對9.11事件及其所帶來的社會政治效應的態度:「我認為也許聽上去有點自相矛盾,但在這樣一個巨大的震撼性事件之後,我們應該鼓足勇氣問一句,它... 用哲学思想理解政治,从哲学史发端之初便已有之。由表及里,从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法律法规整体剖析,高谈阔论气象万千。由里及表,从构成社会元素的个体心理、道德体系、民俗民风展开议论,经世济国心系众生。两者我们都不陌生。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的《欢迎来到实在界... 《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这本书的部分文章在齐泽克的其他书里有经有看过。但一直觉得这个标题真的取得太好了。 熟悉拉康理论的朋友一定知道,拉康的三界论,了解这三界论,就不难知道齐泽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所谓三界是,神,人,妖。。。 sorry,乱入了。。。重来。... “我们缺乏那种语言,无法用它表达我们的不自由。……今天我们用来命名眼前冲突的术语,包括“反恐战争”、“民主和自由”、“人权”等都是假的,都模糊了我们对形势的感知,而不是让我们对之慎思明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享有“自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以之掩饰和维... 这本书里的文字和思想都是前卫的,前卫的可能让一般的读者都无法体会甚至难以接受。作者睿智的思想也同样考验读者的理解力,坦率说,齐泽克这家伙非常善于文字游戏,而这种游戏又的确能在只言片语中留下多许的暇思,让智慧的光芒一直在留白中在读者的思维中徘徊旋转。 ... 在《启蒙辩证法》的结语“进步的代价”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引用了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皮埃尔·弗鲁朗的看法——反对用三氯甲烷进行医疗麻醉。弗鲁朗称,可以证明,麻醉剂只作用于我们记忆的神经网络。简言之,当我们活生生地躺在手术台上被宰割时,我们完全感受到了剧烈的疼痛,但稍后我们醒来时,我们并不记得这段经历。……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这当然是对理性之命运的完美隐喻(这里的理性是以压抑天性为前提的):他的身... 2013-10-11 19:15 6人喜欢 在《启蒙辩证法》的结语“进步的代价”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引用了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皮埃尔·弗鲁朗的看法——反对用三氯甲烷进行医疗麻醉。弗鲁朗称,可以证明,麻醉剂只作用于我们记忆的神经网络。简言之,当我们活生生地躺在手术台上被宰割时,我们完全感受到了剧烈的疼痛,但稍后我们醒来时,我们并不记得这段经历。……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这当然是对理性之命运的完美隐喻(这里的理性是以压抑天性为前提的):他的身体,即主体中的天性部分,完全感受到了这种疼痛,但只是为了进行压抑,主体被迫忘记了。我们支配天性,但天性因此对我们进行了完美的报复:不知不觉中,我们成了自己最大的受害者,我们活生生地屠宰自己。 如果说,“对实在界的激情”是壮丽的实在界之效果(effect of real)的纯粹表象,那么“后现代”对表象的激情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回到“对实在界的激情”那里。不妨以自伤者为例。有一些人(其中多数是女人),觉得有一股难以抗拒的强烈冲动,要用锋利的刀片之类的利器割伤自己。这与我们环境的虚拟化(virtualization of our environment)是并行不悖的:它代表着不顾一切的策略,要拼死回到肉体这个实在界。如此说来,必须把自.. 2014-01-03 23:13 4人喜欢 如果说,“对实在界的激情”是壮丽的实在界之效果(effect of real)的纯粹表象,那么“后现代”对表象的激情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回到“对实在界的激情”那里。不妨以自伤者为例。有一些人(其中多数是女人),觉得有一股难以抗拒的强烈冲动,要用锋利的刀片之类的利器割伤自己。这与我们环境的虚拟化(virtualization of our environment)是并行不悖的:它代表着不顾一切的策略,要拼死回到肉体这个实在界。如此说来,必须把自伤和文身加以对比:文身旨在确保主体进入(虚拟的)符号秩序,而自伤则与之截然相反,旨在张扬现实自身。自伤不是自杀,自伤的行为并不表明自伤者想要自我毁灭。自伤是一种激进的努力,它要(重新)把握现实。或者,从同一现象的另一个方面看,它要把自我牢牢地置身于身体现实之内,同时抵制下列无法承受的焦虑----觉得自己根本不存在似的。自伤者常会说,一看到鲜红的热血从自己割破的伤口中汩汩而出,就会觉得自己依然活着,依然能够脚踏实地。自伤是一种病态的现象,但也是一种病态的努力,它想回归常态,避免彻底的精神崩溃。 按语: 齐先生的书不好读,卖弄与游戏的气质中有着幽暗的味道,一不注意就被他给“懵”了!所以,每次读都是快进、快进,哈 在中文版前言中,齐先生认为“那个无法同化的‘外来物’就是资本这个恶贯满盈、自我驱动的机器”。(2) 2013-02-14 19:15 2人喜欢 按语: 齐先生的书不好读,卖弄与游戏的气质中有着幽暗的味道,一不注意就被他给“懵”了!所以,每次读都是快进、快进,哈 在中文版前言中,齐先生认为“那个无法同化的‘外来物’就是资本这个恶贯满盈、自我驱动的机器”。(2)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企图,因为它想得到“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没有过度的个人主义、社会解体和价值观众相对化的资本主义。 2013-10-12 00:29 2人喜欢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企图,因为它想得到“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没有过度的个人主义、社会解体和价值观众相对化的资本主义。 今天心胸宽广、不拘一格的多元文化主义固然是对他者的体验,但他者又被剥离了他者性。也就是说,他者已被理想化,他们迈着迷人的舞步,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也对现实采取了坚实的整体论的态度。 在我们的日常生存中,我们沉浸于“现实”之中(“现实... 2014-11-09 21:06 一旦我们过于接近被欲求的客体,对色情的痴迷就会变为对赤裸肉体这一实在界的深恶痛绝。自伤是一种病态的现象,但也是一种病态的努力,它想重归常态,避免彻底的精神崩溃。今天心胸宽广、不拘一格的多元文化主义固然是对他者的体验,但他者又被剥离了他者性。也就是说,他者已被理想化,他们迈着迷人的舞步,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也对现实采取了坚实的整体论的态度。在我们的日常生存中,我们沉浸于“现实”之中(“现实”是由幻象构造和支撑的),但沉浸于“现实”的我们受到了征兆(symptoms)的侵扰。征兆证明,我们心灵的另一个层面,也是被压抑的层面,正在抵制我们,使我们无法沉浸于“现实”。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穿越幻象”意味着,使自己完全认同幻象。幻象既可以抚慰人心,令人心平气和,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想象性场景,能使我们忍受大对体的欲望这个深渊(abyss of the Other's desire);同时又可以粉碎、扰乱我们的现实,与我们的现实水火不容。必须直接面对符号空间中大行其道的淫荡幻象,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认同这些幻象。不能因为这些幻象并不代表人们的“真实面目”,而将这些幻象的淫荡性拒之门外。与此相比,更为困难的是,在“真正”的现实中识别出虚构的部分。以为她展示自己的幻象就是组成防守阵形以抗拒正常性行为,以为她展示自己的幻象足以表明她无法促成并享受性行为,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误导。恰恰相反,展示出来的幻象构成了她的存在内核。这幻象“在她之内,却又大于她”。只有性行为才真正组成了防守阵形,抵抗以幻象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威胁。受虐者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为大对体提供原乐,而是令其焦虑。也就是说,尽管受虐者心甘情愿地忍受大对体的折磨,尽管受虐者要对大对体毕恭毕敬,使自己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但真正制订规则的是他自己。我们应该接受下列驳论:要真正忘记某个事件,必须首先倾尽全力,牢牢地记住它。为了说明这个驳论,我们要记住,与存在相对的不是非存在,而是坚持存在:它并不存在,它继续坚持存在,力争成为存在。如果我错过了一个事关生死的伦理机会,没能采取那个足以“改变一切”的行动,那个非存在,即我本来应该采取却没有采取的行动,会永远令我寝食难安:尽管我没有采取的行动并不存在,它的幽灵却在持续地坚持存在。错失了革命的机会就会留下空白,这样的空白会在“非理性”的破坏性愤怒的发作中爆发。20世纪的“对实在界的激情”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对实在界的激情”;它的问题在于,它是一种虚假的激情,它对隐藏在表象之后的实在界的冷酷追寻,是皆在避免面对实在界的终极策略。“这些人怎么会如此展示和实施对自己生命的漠视?”难免要想,这种诧异的另一面,是一个相当可悲的事实:生活在第一世界国家的我们,发现越来越难以设想一种我们乐意奉献生命的公共事业或普遍事业。这时发生的突变完全是符号性的,“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变化。目前处于主流的视点还是纯真凝视(innocent gaze)的视点,还是纯真的凝视开始面对从外部闯入的难以言表的邪恶。关于这种凝视,我们应该鼓起勇气,把黑格尔的著名格言运用到它的身上:邪恶(还)居于感知周围邪恶的纯真凝视的内部。把自己与自己反对的东西关联起来,把自己也归入犯罪现场,是唯一真正的“无限正义”。用阿兰 巴迪欧的话说,幸福不属于“真”(truth)的范畴,而属于“纯粹的存在”(mere being)的王国。也就是说,幸福本身也是混乱不堪、模糊不清和前后矛盾的。刺穿了社会躯体的“垂直”对抗总是受到严格的审查,总是要被替换,或翻译成完全不同的“水平”差异,我们也必须学着容忍差异,因为差异可以互补。在这里,潜在的本体论视境是,特定星系具有不可削减的多元性。星系在增加和位移,但永远无法把它们置于中立的通用容器之内。就在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个层面的时候,好莱坞满足了一种需求,即对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进行最为激进的后殖民批判。在那里,核心问题被设想为不可能获得的普遍性,我们不应把自己对普遍性的看法(如普遍人权等)强加于人,而是要把普遍性——即不同文化之间共有的理解空间(space of understanding)——视为无穷无尽的翻译过程,视为对我们个人的特定立场的持续改写。是否有必要再补充一句,对普遍性的这种看法——即把普遍性视为无穷无尽的翻译过程——无论如何都与某些神奇时刻的到来毫无关系?一旦这些神奇时刻到来,有效的普遍性会假借破坏性的伦理—政治行为以暴力的形式显现出来。实际的普遍性不是永远无法获得的中立的文化翻译空间,而是对下列过程的体验——我们跨越了文化的鸿沟,分享同一个对抗。今天的霸权态度是“抵抗”:有关分崩离析的、被边缘化的性“多数”、种族“多数”和行为“多数”(包括同性恋、精神病患者和囚犯等)的诗学,都在“抵抗”神秘的中央权力。……因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就此得出如下结论:“抵抗”话语如今已经成为常态,因而也成了主要的障碍,它在阻止真正质疑主流关系的新兴话语的出现?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抨击这种霸权态度的内核,即抨击这样的观念——“尊重他人”是最基本的伦理公理。尊重他人的彻底他者性(radical Otherness),在他和或她身上,永远是存在着他人身上的难以渗透的深渊,这个绝对(Absolute)。20世纪的极权主义,以其数百万的受害者,向我们表明:始终追随我们所谓的“主观上正当的行动”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多元性和多样性是面具。之所以重视这副面具,当然与今天全球生活的潜在单调性有关系。他想利用和操纵别人,到头来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们认为自己在嘲弄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实呢,我们这样做,只是强化了它对我们的控制而已。事实上被审判的恰恰是这些“激进左翼”,因为他们在检测自己有关后南斯拉夫战争的认识时一败涂地。他献出了人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神的不存在。他没有把自己的祭品献给祭坛。他献出祭品,只是为了宣称:祭坛只是摆设,神位空空如也。一旦我们试图保护真正秘密的隐私领域,反对工具性/客观化的、“异化”的公开交易的冲击,隐私就会成为彻底客观化的、“商品化”的领域。现在,退回隐私领域意味着接受最近兴起的文化工业大肆宣传的隐私本真性公式:从聆听精神启蒙课程,到追逐最新的文化时尚或其他时尚,再到慢跑和健身。退回隐私领域,其终极真相就是在电视节目上公开自己内心的秘密。与强调这话总隐私不同,我们应该强调,现在要摆脱“异化”的商品化,那就是创造新的集体性。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提供的教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有用:对一对情侣来说,建立亲密无间、令人满足的私人(性)关系的方式——唯一方式——不是彼此凝视对方的眼睛,忘记四周的世界,而是手拉着手,一起看着身外的某处,即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事情,共同舍身投入的事业。全球主体化的最终结果不是“客观现实”消失了,而是我们的主体性消失了,主体性变成了琐碎的奇思怪想,社会现实则依然故我。在这里,我禁不住要重述审讯者对温斯顿·史密斯所提问题的回答。温斯顿·史密斯怀疑老大哥根本不存在,审讯者的回答是:“不存在的是你!”有人对意识形态大对体的存在持后现代式怀疑,对他们的恰当回答是:不存在的是主体本身。实证主义的终极受害者并非混乱不堪的形而上学概念,而是事实本身;对世俗化的激进追求,投身于世俗生活,已经把今生今世转化成了“抽象”、贫血的过程。“末人”、“后现代”的个人认为所有“高尚”目标都是恐怖主义的,并对之加以拒绝。他们倾其一生致力于活着,致力于过上这样的生活——充满了越来越精致的、由人工刺激或诱发的小快乐。只要“死”和“生”为圣保罗指定的是两种生存(主体)立场,而不是两种“客观”事实,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提出同样的圣保罗式的问题:如今究竟有谁真正活着?他或她的强迫性仪式的终极目的,不就是阻止某件“事情”发生吗?而且这件“事情”不就是生活的过度吗?他或她害怕发生的灾难,不就是最终真的发生在他或她身上的某件事情?对立的两极不仅相互支持,甚至复制对方的结构。今天,新世界秩序把自己展示为包容差异的世界,不同文化共存的世界。与此同时,敌人被描述为狂热的/不宽容的、排外的人。在“被控世界”中,对主观自由的体验只是一种表象,其实质是屈从于规训机制。归根结底,“被控世界”这一“极权主义”概念是有关个人自主和自由的“官方”公共意识形态(与实践)的、充斥着淫荡和幻想的黑暗面:第一个(即“被控世界”)必定陪伴着第二个(即自主与自由),补充第二个,成为它淫荡的、阴影般的孪生子。弗卢朗声称,可以证明,麻醉剂只作用于我们记忆的神经网络。简言之,当我们活生生地躺在手术台上被宰割时,我们完全感受到了剧烈的疼痛,但稍后我们醒来时,我们并不记得这段经历。即使(或者更确切些说,正是)这样,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这个绝望的选择提升为普遍的原则。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几个月里,从曼哈顿商业中心到第20大街,都会闻到世贸中心双子塔烧焦的味道。人们迷恋这种味道。它开始充当拉康会称之为纽约“症候”的东西,即压缩了主体对这座城市的力比多依恋的密码。所以,这味道一旦消失,人们会依依不舍,正是诸如此类的细节,证实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挚爱。只有在出现下列情形时,这种爱才会成为问题:人们开始怀疑,为什么其他人不能完全分享美国的痛苦?牺牲自我(Ego)的前提下,超我(社会权威)和本我(非法的攻击驱力)直接达成的变态的合约。 如果说,“对实在界的激情”是壮丽的实在界之效果(effect of real)的纯粹表象,那么“后现代”对表象的激情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回到“对实在界的激情”那里。不妨以自伤者为例。有一些人(其中多数是女人),觉得有一股难以抗拒的强烈冲动,要用锋利的刀片之类的利器割伤自己。这与我们环境的虚拟化(virtualization of our environment)是并行不悖的:它代表着不顾一切的策略,要拼死回到肉体这个实在界。如此说来,必须把自.. 2014-01-03 23:13 4人喜欢 如果说,“对实在界的激情”是壮丽的实在界之效果(effect of real)的纯粹表象,那么“后现代”对表象的激情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回到“对实在界的激情”那里。不妨以自伤者为例。有一些人(其中多数是女人),觉得有一股难以抗拒的强烈冲动,要用锋利的刀片之类的利器割伤自己。这与我们环境的虚拟化(virtualization of our environment)是并行不悖的:它代表着不顾一切的策略,要拼死回到肉体这个实在界。如此说来,必须把自伤和文身加以对比:文身旨在确保主体进入(虚拟的)符号秩序,而自伤则与之截然相反,旨在张扬现实自身。自伤不是自杀,自伤的行为并不表明自伤者想要自我毁灭。自伤是一种激进的努力,它要(重新)把握现实。或者,从同一现象的另一个方面看,它要把自我牢牢地置身于身体现实之内,同时抵制下列无法承受的焦虑----觉得自己根本不存在似的。自伤者常会说,一看到鲜红的热血从自己割破的伤口中汩汩而出,就会觉得自己依然活着,依然能够脚踏实地。自伤是一种病态的现象,但也是一种病态的努力,它想回归常态,避免彻底的精神崩溃。 今天心胸宽广、不拘一格的多元文化主义固然是对他者的体验,但他者又被剥离了他者性。也就是说,他者已被理想化,他们迈着迷人的舞步,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也对现实采取了坚实的整体论的态度。 在我们的日常生存中,我们沉浸于“现实”之中(“现实... 2014-11-09 21:06 一旦我们过于接近被欲求的客体,对色情的痴迷就会变为对赤裸肉体这一实在界的深恶痛绝。自伤是一种病态的现象,但也是一种病态的努力,它想重归常态,避免彻底的精神崩溃。今天心胸宽广、不拘一格的多元文化主义固然是对他者的体验,但他者又被剥离了他者性。也就是说,他者已被理想化,他们迈着迷人的舞步,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也对现实采取了坚实的整体论的态度。在我们的日常生存中,我们沉浸于“现实”之中(“现实”是由幻象构造和支撑的),但沉浸于“现实”的我们受到了征兆(symptoms)的侵扰。征兆证明,我们心灵的另一个层面,也是被压抑的层面,正在抵制我们,使我们无法沉浸于“现实”。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穿越幻象”意味着,使自己完全认同幻象。幻象既可以抚慰人心,令人心平气和,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想象性场景,能使我们忍受大对体的欲望这个深渊(abyss of the Other's desire);同时又可以粉碎、扰乱我们的现实,与我们的现实水火不容。必须直接面对符号空间中大行其道的淫荡幻象,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认同这些幻象。不能因为这些幻象并不代表人们的“真实面目”,而将这些幻象的淫荡性拒之门外。与此相比,更为困难的是,在“真正”的现实中识别出虚构的部分。以为她展示自己的幻象就是组成防守阵形以抗拒正常性行为,以为她展示自己的幻象足以表明她无法促成并享受性行为,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误导。恰恰相反,展示出来的幻象构成了她的存在内核。这幻象“在她之内,却又大于她”。只有性行为才真正组成了防守阵形,抵抗以幻象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威胁。受虐者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为大对体提供原乐,而是令其焦虑。也就是说,尽管受虐者心甘情愿地忍受大对体的折磨,尽管受虐者要对大对体毕恭毕敬,使自己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但真正制订规则的是他自己。我们应该接受下列驳论:要真正忘记某个事件,必须首先倾尽全力,牢牢地记住它。为了说明这个驳论,我们要记住,与存在相对的不是非存在,而是坚持存在:它并不存在,它继续坚持存在,力争成为存在。如果我错过了一个事关生死的伦理机会,没能采取那个足以“改变一切”的行动,那个非存在,即我本来应该采取却没有采取的行动,会永远令我寝食难安:尽管我没有采取的行动并不存在,它的幽灵却在持续地坚持存在。错失了革命的机会就会留下空白,这样的空白会在“非理性”的破坏性愤怒的发作中爆发。20世纪的“对实在界的激情”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对实在界的激情”;它的问题在于,它是一种虚假的激情,它对隐藏在表象之后的实在界的冷酷追寻,是皆在避免面对实在界的终极策略。“这些人怎么会如此展示和实施对自己生命的漠视?”难免要想,这种诧异的另一面,是一个相当可悲的事实:生活在第一世界国家的我们,发现越来越难以设想一种我们乐意奉献生命的公共事业或普遍事业。这时发生的突变完全是符号性的,“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变化。目前处于主流的视点还是纯真凝视(innocent gaze)的视点,还是纯真的凝视开始面对从外部闯入的难以言表的邪恶。关于这种凝视,我们应该鼓起勇气,把黑格尔的著名格言运用到它的身上:邪恶(还)居于感知周围邪恶的纯真凝视的内部。把自己与自己反对的东西关联起来,把自己也归入犯罪现场,是唯一真正的“无限正义”。用阿兰 巴迪欧的话说,幸福不属于“真”(truth)的范畴,而属于“纯粹的存在”(mere being)的王国。也就是说,幸福本身也是混乱不堪、模糊不清和前后矛盾的。刺穿了社会躯体的“垂直”对抗总是受到严格的审查,总是要被替换,或翻译成完全不同的“水平”差异,我们也必须学着容忍差异,因为差异可以互补。在这里,潜在的本体论视境是,特定星系具有不可削减的多元性。星系在增加和位移,但永远无法把它们置于中立的通用容器之内。就在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个层面的时候,好莱坞满足了一种需求,即对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进行最为激进的后殖民批判。在那里,核心问题被设想为不可能获得的普遍性,我们不应把自己对普遍性的看法(如普遍人权等)强加于人,而是要把普遍性——即不同文化之间共有的理解空间(space of understanding)——视为无穷无尽的翻译过程,视为对我们个人的特定立场的持续改写。是否有必要再补充一句,对普遍性的这种看法——即把普遍性视为无穷无尽的翻译过程——无论如何都与某些神奇时刻的到来毫无关系?一旦这些神奇时刻到来,有效的普遍性会假借破坏性的伦理—政治行为以暴力的形式显现出来。实际的普遍性不是永远无法获得的中立的文化翻译空间,而是对下列过程的体验——我们跨越了文化的鸿沟,分享同一个对抗。今天的霸权态度是“抵抗”:有关分崩离析的、被边缘化的性“多数”、种族“多数”和行为“多数”(包括同性恋、精神病患者和囚犯等)的诗学,都在“抵抗”神秘的中央权力。……因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就此得出如下结论:“抵抗”话语如今已经成为常态,因而也成了主要的障碍,它在阻止真正质疑主流关系的新兴话语的出现?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抨击这种霸权态度的内核,即抨击这样的观念——“尊重他人”是最基本的伦理公理。尊重他人的彻底他者性(radical Otherness),在他和或她身上,永远是存在着他人身上的难以渗透的深渊,这个绝对(Absolute)。20世纪的极权主义,以其数百万的受害者,向我们表明:始终追随我们所谓的“主观上正当的行动”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多元性和多样性是面具。之所以重视这副面具,当然与今天全球生活的潜在单调性有关系。他想利用和操纵别人,到头来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们认为自己在嘲弄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实呢,我们这样做,只是强化了它对我们的控制而已。事实上被审判的恰恰是这些“激进左翼”,因为他们在检测自己有关后南斯拉夫战争的认识时一败涂地。他献出了人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神的不存在。他没有把自己的祭品献给祭坛。他献出祭品,只是为了宣称:祭坛只是摆设,神位空空如也。一旦我们试图保护真正秘密的隐私领域,反对工具性/客观化的、“异化”的公开交易的冲击,隐私就会成为彻底客观化的、“商品化”的领域。现在,退回隐私领域意味着接受最近兴起的文化工业大肆宣传的隐私本真性公式:从聆听精神启蒙课程,到追逐最新的文化时尚或其他时尚,再到慢跑和健身。退回隐私领域,其终极真相就是在电视节目上公开自己内心的秘密。与强调这话总隐私不同,我们应该强调,现在要摆脱“异化”的商品化,那就是创造新的集体性。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提供的教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有用:对一对情侣来说,建立亲密无间、令人满足的私人(性)关系的方式——唯一方式——不是彼此凝视对方的眼睛,忘记四周的世界,而是手拉着手,一起看着身外的某处,即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事情,共同舍身投入的事业。全球主体化的最终结果不是“客观现实”消失了,而是我们的主体性消失了,主体性变成了琐碎的奇思怪想,社会现实则依然故我。在这里,我禁不住要重述审讯者对温斯顿·史密斯所提问题的回答。温斯顿·史密斯怀疑老大哥根本不存在,审讯者的回答是:“不存在的是你!”有人对意识形态大对体的存在持后现代式怀疑,对他们的恰当回答是:不存在的是主体本身。实证主义的终极受害者并非混乱不堪的形而上学概念,而是事实本身;对世俗化的激进追求,投身于世俗生活,已经把今生今世转化成了“抽象”、贫血的过程。“末人”、“后现代”的个人认为所有“高尚”目标都是恐怖主义的,并对之加以拒绝。他们倾其一生致力于活着,致力于过上这样的生活——充满了越来越精致的、由人工刺激或诱发的小快乐。只要“死”和“生”为圣保罗指定的是两种生存(主体)立场,而不是两种“客观”事实,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提出同样的圣保罗式的问题:如今究竟有谁真正活着?他或她的强迫性仪式的终极目的,不就是阻止某件“事情”发生吗?而且这件“事情”不就是生活的过度吗?他或她害怕发生的灾难,不就是最终真的发生在他或她身上的某件事情?对立的两极不仅相互支持,甚至复制对方的结构。今天,新世界秩序把自己展示为包容差异的世界,不同文化共存的世界。与此同时,敌人被描述为狂热的/不宽容的、排外的人。在“被控世界”中,对主观自由的体验只是一种表象,其实质是屈从于规训机制。归根结底,“被控世界”这一“极权主义”概念是有关个人自主和自由的“官方”公共意识形态(与实践)的、充斥着淫荡和幻想的黑暗面:第一个(即“被控世界”)必定陪伴着第二个(即自主与自由),补充第二个,成为它淫荡的、阴影般的孪生子。弗卢朗声称,可以证明,麻醉剂只作用于我们记忆的神经网络。简言之,当我们活生生地躺在手术台上被宰割时,我们完全感受到了剧烈的疼痛,但稍后我们醒来时,我们并不记得这段经历。即使(或者更确切些说,正是)这样,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这个绝望的选择提升为普遍的原则。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几个月里,从曼哈顿商业中心到第20大街,都会闻到世贸中心双子塔烧焦的味道。人们迷恋这种味道。它开始充当拉康会称之为纽约“症候”的东西,即压缩了主体对这座城市的力比多依恋的密码。所以,这味道一旦消失,人们会依依不舍,正是诸如此类的细节,证实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挚爱。只有在出现下列情形时,这种爱才会成为问题:人们开始怀疑,为什么其他人不能完全分享美国的痛苦?牺牲自我(Ego)的前提下,超我(社会权威)和本我(非法的攻击驱力)直接达成的变态的合约。 根据古希腊神话,欧罗巴(Europa)是腓尼基的公主,曾经遭到变身为公牛的宙斯的拐骗和强暴,难怪她的名字的意思是“沮丧之人”(the dismal one)。这难道不是欧洲的真实写照?(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概念的)欧洲不就是西方野蛮人两次拐骗东方艺术之珠(Eastern pearl)的结果吗?两次拐骗,一次是罗马人对已经庸俗化的希腊思想的拐骗,一次是野蛮的西方人在中世纪初对基督教的拐骗,并使之庸俗化。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不是有点像第三次拐... 2014-01-07 16:26 根据古希腊神话,欧罗巴(Europa)是腓尼基的公主,曾经遭到变身为公牛的宙斯的拐骗和强暴,难怪她的名字的意思是“沮丧之人”(the dismal one)。这难道不是欧洲的真实写照?(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概念的)欧洲不就是西方野蛮人两次拐骗东方艺术之珠(Eastern pearl)的结果吗?两次拐骗,一次是罗马人对已经庸俗化的希腊思想的拐骗,一次是野蛮的西方人在中世纪初对基督教的拐骗,并使之庸俗化。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不是有点像第三次拐骗?美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欧洲展开了逐渐的、漫长的殖民化过程,“反恐战争”不就是这个过程的可恶结局和“神来之笔”吗?现在欧洲不是再一次遭到了西方--美国文明--的绑架?美国不正在全球制定准则,并把欧洲视为自己的一个省?欧洲人拐了希腊思想,使之庸俗化,欧洲人在中世纪弄走了东方的基督教,东方还有老毛子的东正教!然后欧洲人的对美洲大陆殖民,现在美国反噬欧洲,这.... 一个苏联政治笑话,以前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尼克松访问勃列日涅夫时看到一台特殊的电话,勃列日涅夫向他解释说,这个电话是用来打给地狱的。在笑话的结尾处,尼克松抱怨,打往地狱的电话费实在不菲。勃列日涅夫平静地回答道:“我们是苏联人,对我们来说,打电话给地狱,只需要支付本地话费。” 2014-01-06 10:56 一个苏联政治笑话,以前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尼克松访问勃列日涅夫时看到一台特殊的电话,勃列日涅夫向他解释说,这个电话是用来打给地狱的。在笑话的结尾处,尼克松抱怨,打往地狱的电话费实在不菲。勃列日涅夫平静地回答道:“我们是苏联人,对我们来说,打电话给地狱,只需要支付本地话费。” 免责申明:
本站仅提供学习的平台,所有资料均来自于网络,版权归原创者所有!本站不提供任何保证,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果对您的版权或者利益造成损害,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尽快予以处理。
|



